今年 6 月底,馬斯克的 Neuralink 開了一場(chǎng)發(fā)布會(huì),展示了其在腦機(jī)接口領(lǐng)域的最新進(jìn)展,比如,7 位植入腦機(jī)接口的患者,僅憑意念就能打字、玩游戲,甚至操控機(jī)械臂。
7 月,這個(gè)數(shù)字增加到了 9 例。
同時(shí)據(jù)《 金融時(shí)報(bào) 》報(bào)道,OpenAI 及其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始人山姆?奧特曼也正準(zhǔn)備投資一家名為 Merge Labs 的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,這個(gè)公司類似于 Neuralink,也是專注于腦機(jī)接口方向。
當(dāng)國(guó)外科技巨頭們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腦機(jī)接口研究之際,國(guó)內(nèi)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進(jìn)展如何呢?
為了探究這個(gè)問題,知危聯(lián)系了腦機(jī)接口行業(yè)從業(yè)人員、頭部類腦研究所專家、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企業(yè) CEO 等多位相關(guān)人士進(jìn)行對(duì)話,試圖去了解國(guó)內(nèi)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進(jìn)展以及具體應(yīng)用領(lǐng)域。

目前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主要分兩種方式:侵入式和非侵入式,區(qū)別在于硬件是否入腦。不管是侵入式或非侵入式,整個(gè)調(diào)控過程都可以大致分為,采集信號(hào)、解析信號(hào)和輸入信號(hào)等環(huán)節(jié)。
“ 馬斯克那個(gè) Neuralink 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侵入式,國(guó)內(nèi)做同類型的公司也有,但做得更多的還是非侵入式的。” 某腦機(jī)接口行業(yè)從業(yè)者 David 告訴知危。
“ 侵入式的話,采集到的信號(hào)會(huì)更準(zhǔn)確一些,畢竟它是開顱植入到腦部。而像非侵入式的話,大家可能會(huì)更熟悉,就是頭上戴一些電極或者通道來采集腦電的信號(hào),然后在電腦端去做信號(hào)的處理和降噪,之后再根據(jù)實(shí)際的應(yīng)用,選擇怎么信號(hào)輸出和執(zhí)行。”
從技術(shù)角度來說,侵入式的微電極能直接讀取皮層神經(jīng)元電信號(hào),而非侵入式只能采集穿過顱骨后的衰減信號(hào),這導(dǎo)致兩者之間會(huì)產(chǎn)生 30 倍以上的信噪比差異。
據(jù) David 所說,國(guó)內(nèi)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目前商業(yè)化比較順利的還是做非侵入式,主要是集中在助眠、正念、情緒調(diào)節(jié)等領(lǐng)域,而侵入式則大多是在實(shí)驗(yàn)室階段,研究的方向也各不相同。
“ 光是醫(yī)療上就很多方向的,像什么治老年癡呆的,帕金森的,抑郁癥的,馬斯克不也是在做癱瘓治療和盲人復(fù)明,其中國(guó)內(nèi)這些方向都有人做。” 上海復(fù)旦大學(xué)類腦研究院醫(yī)學(xué)工程項(xiàng)目主管岳麟這樣對(duì)知危說道。
“ 我們是研究 DBS ( Deep Brain Stimulation,深部腦刺激 )的,只做 DBS 。主要是用來治療很多神經(jīng)性疾病,就像阿爾茲海默癥那種腦萎縮,就是神經(jīng)異常了,它神經(jīng)通路沒有損傷,但是神經(jīng)信號(hào)出來是異常的,這個(gè)時(shí)候是要刺激的。我們組就是做刺激,看能不能把信號(hào)給你調(diào)節(jié)過來。”
岳麟介紹道,Neuralink 主要是做修復(fù),不管是治癱瘓和復(fù)明,其實(shí)都是神經(jīng)修復(fù),通過信號(hào)的輸入來把中間斷掉的那部分神經(jīng)信號(hào)給接起來達(dá)到治療的效果,深部腦刺激的話會(huì)比神經(jīng)修復(fù)更難一點(diǎn)。
“ 咱們國(guó)內(nèi)科學(xué)研究領(lǐng)域和國(guó)外沒什么差距的。他們?cè)谘芯渴裁次覀円苍谘芯渴裁础4蠹叶际悄X部有些地方突破不了,現(xiàn)在很多的腦部信號(hào)都搞不明白,雖然能采回來,但是原理是什么,工作機(jī)理是啥,還沒搞明白。”
David 也表達(dá)了同樣的觀點(diǎn),“ 前幾天我還參加了一個(gè)關(guān)于人工智能的論壇會(huì),會(huì)上有個(gè)院士就是腦機(jī)接口的專家,他也講到,就算你后續(xù)提高了解碼信號(hào)的技術(shù),但是人類是一個(gè)有情感的動(dòng)物,你情感的表達(dá)是如何通過腦電信號(hào)去表現(xiàn)依然還是有很多未被人類了解的。”
目前制約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的主要原因,還是大腦太神秘了。可能采集的一些腦電信號(hào),實(shí)際上都不是腦電信號(hào),還要把一些非標(biāo)準(zhǔn)的腦活動(dòng)信號(hào)剔除,然后再對(duì)應(yīng)解碼腦電信號(hào)到具體的人的某些行動(dòng),而這方面的數(shù)據(jù)太大了,到現(xiàn)在也沒有公司在做這種底層的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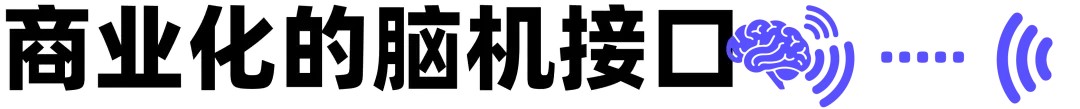
在前沿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科學(xué)研究領(lǐng)域還在努力突破之際,市場(chǎng)端的商業(yè)化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。
“ 對(duì)于信號(hào)的采集和解析,國(guó)內(nèi)做這部分的公司已經(jīng)有很多,技術(shù)上也相對(duì)成熟了,不同之處可能在于,大家選擇給用戶帶去什么價(jià)值,解決什么問題。” 慕眠科技創(chuàng)始人兼 CEO 孔祥這樣跟知危說道。
“ 我們公司主要是在非侵入式領(lǐng)域提供算法技術(shù)。我們的算法主要負(fù)責(zé),信號(hào)數(shù)據(jù)解析之后的干預(yù)輸入,與腦機(jī)接口公司合作對(duì)用戶進(jìn)行聽覺刺激,達(dá)到助眠、情緒調(diào)節(jié)、提升專注力等效果。”
整個(gè)流程就是先采集用戶腦電波的數(shù)據(jù)特征,進(jìn)行一些定性的分析,給出針對(duì)性的能夠去調(diào)控和干預(yù)的音樂,再通過播放設(shè)備影響用戶的腦電波變化來達(dá)到助眠的效果。
“ 這種干預(yù)方式是更溫和的,或者說是危險(xiǎn)性最低的,用戶也比較能接受。當(dāng)然如果是要實(shí)時(shí)調(diào)控的話,也還是需要專業(yè)的設(shè)備,比如腦控頭環(huán),而不需要實(shí)時(shí)調(diào)控的話,用手機(jī)播放也可以。”
對(duì)于大部分人來說,關(guān)于腦機(jī)接口的印象可能還是科幻電影里,人通過腦子里插個(gè)芯片,就可以實(shí)現(xiàn)在腦內(nèi)與各種事物進(jìn)行交互,而如果說現(xiàn)在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更多的商業(yè)化應(yīng)用還是在助眠,冥想等方面,這難免會(huì)有些心理落差。
孔祥解釋道,“ 還是一個(gè)階段性發(fā)展的問題,影視作品里呈現(xiàn)的那種情況,已經(jīng)是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里很成熟階段的場(chǎng)景。現(xiàn)在的話其實(shí)也能實(shí)現(xiàn),用大腦意念去打字、去控制飛行器的飛行、去讓聾啞人發(fā)聲等,但這些都還是實(shí)驗(yàn)室案例,技術(shù)上還沒達(dá)到一個(gè)大規(guī)模商用的階段。”
“ 睡眠和情緒這一塊,雖然看起來跟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這么深?yuàn)W的一個(gè)學(xué)科相比會(huì)顯得很小,微不足道,但是目前來看的話,這是一個(gè)大眾級(jí)的能夠去接受,去使用的比較好的切入口。未來更多的應(yīng)用,肯定是需要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,產(chǎn)品本身工業(yè)化的發(fā)展,以及用戶更深的一些需求的挖掘,慢慢去成長(zhǎng)起來。”
當(dāng)提到 Meta 正在嘗試把腦機(jī)接口應(yīng)用在社交方面,比如直接在 Facebook 上發(fā)送 “ 腦電波信息 ” 時(shí),孔祥表示社交方面應(yīng)用的話,可能涉及到親密關(guān)系會(huì)更容易商業(yè)化一些。
“ 之前我們接觸過一家公司,它是拿腦機(jī)來做什么呢?來做相親。就是兩個(gè)人帶上腦機(jī)設(shè)備之后,看互相的信號(hào),兩個(gè)人之間是否有同頻共振的東西,然后看兩個(gè)人是否有緣分、一見鐘情等等。如果做這種產(chǎn)品的話,我覺得還是有機(jī)會(huì)得到大眾喜歡的。但是常規(guī)一些的,你比如說用來發(fā)個(gè)微博、回微信或者郵件什么的話,我認(rèn)為目前還不足以打動(dòng)消費(fèi)者。”
孔祥還提到目前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也有應(yīng)用在安全領(lǐng)域,包括像公交車司機(jī)、飛行員、火車駕駛員以及礦業(yè)礦產(chǎn)方面工作人員,就可以通過腦機(jī)設(shè)備進(jìn)行非常實(shí)時(shí)的數(shù)據(jù)采集和預(yù)警,避免一些安全的隱患和事故。
孔祥認(rèn)為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在康養(yǎng)、日常生活或者臨床上要達(dá)到影視作品里設(shè)想的那種體驗(yàn),至少還得以十年為單位,而如果只是具體到某些疾病的臨床應(yīng)用,那么未來三五年可能就可以實(shí)現(xiàn)了。
“ 今年國(guó)家政策放開之后,很多地方醫(yī)院都已經(jīng)在開展這個(gè)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的研究、臨床的實(shí)驗(yàn)了,所以這個(gè)不會(huì)太久。”

“ 現(xiàn)在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這個(gè)領(lǐng)域還沒有出現(xiàn)特別強(qiáng)的公司能解碼大部分領(lǐng)域的腦電信號(hào),大家都還在各自細(xì)分的那個(gè)方向上研究,如果真的有公司能在通用層面實(shí)現(xiàn)解碼之后,可能在后續(xù)的應(yīng)用端就會(huì)一下子爆發(fā)出來。”
關(guān)于腦機(jī)接口之后的方向以及應(yīng)用場(chǎng)景,David描繪道。
“ 我覺得它在各個(gè)各行業(yè)的應(yīng)用還是有很多場(chǎng)景的,比如在人機(jī)交互及工業(yè)應(yīng)用方面的話,像腦控打字、腦控輪椅,腦控機(jī)器人、腦控?zé)o人機(jī),這些都是有可能實(shí)現(xiàn)的,只是說在現(xiàn)現(xiàn)階段它可能技術(shù)還沒有達(dá)到。”
“ 醫(yī)療方面的話,像抑郁癥、多動(dòng)癥、孤獨(dú)癥、癲癇,就神經(jīng)系統(tǒng)相關(guān)的疾病都能夠輔助進(jìn)行一些診斷或和干預(yù),包括一些肢體康復(fù)治療,教育的話其實(shí)也有很多,像強(qiáng)腦科技正在做的一些事,比如對(duì)認(rèn)知能力的一些提升,腦潛力的一些開發(fā),他們會(huì)檢測(cè)不同腦部位的活躍程度,額葉枕葉都會(huì)監(jiān)測(cè),然后有針對(duì)性地做一些教育培訓(xùn)。”
“ 還有就是在娛樂領(lǐng)域,像巖思類腦他們有做用非侵入式設(shè)備來打黑神話悟空,至于現(xiàn)在用得最多的助眠,以后還可能發(fā)展到在睡夢(mèng)中刺激,然后給你一些不同的夢(mèng)境,這些我覺得還是有很大潛力的。”
在提到目前商業(yè)化方面,David 則表示對(duì)比 Neuralink 的技術(shù),國(guó)內(nèi)很多公司差距還蠻大的。
“ 像國(guó)內(nèi)也有做腦電芯片的公司,雖然說它的通道( 采集信號(hào)的一種方式 )數(shù)值很高,但是它那個(gè)大小比硬幣都要大多了。那種芯片植入到腦部的話,它損傷還是很大的。其次 Neuralink 為了讓芯片植入大腦,還專門研發(fā)了一個(gè)很精準(zhǔn)的植入設(shè)備。在我看來,光是硬件上國(guó)內(nèi)很多做侵入式的公司都還遠(yuǎn)遠(yuǎn)沒有達(dá)到它那個(gè)水平。”
David 還表示,在腦電信號(hào)采集上,雖然說大家都比較成熟,但還是有區(qū)別的,有的公司用的 256 通道腦電帽戴在頭上,有的公司要把頭發(fā)剃光,用 128 通道的,還有的公司只是用了三個(gè)電極片就可以采集腦電信號(hào)。
而在目前腦機(jī)閉環(huán)調(diào)控應(yīng)用得最多的冥想、助眠方面的產(chǎn)品,某業(yè)內(nèi)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南天表示,效果也是因人而異。
“ 我用過行業(yè)里邊很多這種東西,因人而異吧,就像某個(gè)助眠的產(chǎn)品,有的人睡不著可能聽一聽有用。像我這種只要閉上眼幾秒鐘我就睡著了,它對(duì)我來說就是個(gè)噪聲。”
關(guān)于腦機(jī)接口行業(yè)的現(xiàn)狀和未來,南天說道:“ 目前腦機(jī)接口還缺少那么一個(gè) ‘ DeepSeek 時(shí)刻 ’,就是類似于出現(xiàn)一個(gè)通用的平臺(tái)或者說是 Agent,它可以把大部分這種信號(hào)的采集和解碼都統(tǒng)一去開源,然后在這種層面上,大家各自去做你自己想象的那種商業(yè)化落地,我覺得這個(gè)就可能會(huì)是比較好的一種情況。”

